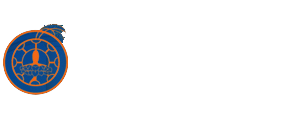大慧宗杲的師承
臨濟宗,始創於臨濟義玄大師,是洪州宗馬祖道一門下分出的宗派。義玄是黄蘗希運禪師的法嗣,他上承六祖惠能,歷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黃蘗希運的禪法,以機鋒凌厲,棒喝峻烈的禪風聞名於世。臨濟宗傳至宋代,石霜楚圓門下弟子慧南、方會二人,開創了黃龍派、楊歧派。從此,禪家才有五家七宗之名。南宋時,因為楊岐派傳人大慧宗杲大力提倡話頭禪,他的的影響力使得臨濟宗一支獨秀,成為禪宗與漢傳佛教最具代表性的宗派。大慧宗杲,起先是跟從曹洞宗洞山微禪師學禪,但因緣不契合,再依寶峰山湛堂文准禪師。文准是黃龍派真淨克文的弟子,宗杲前後依止六年,在思想上是深受他的老師影響,特別是文准將禪學與儒家倫理學說的結合,重視禪的現世性品格的理路,這對宗杲後來提出「忠義之說」有直接的影響。宗杲在寶峰錘煉六年,在禪路上大有進境,文准囑付他再參訪圓悟克勤。圓悟批評他還存在著對語言文字的執著,鼓勵他要參活句,莫參死句,應該在「無所攀附、無所支撐」(即「懸崖撒手」)處去參悟、體認。圓悟認為他是可以振興臨濟正宗的人,於是將自己所著《臨濟正宗說》付囑宗杲,令他掌記室,並讓他分座訓徒。
宗杲創立「話頭禪」
宗杲在臨濟宗思想發展史上的貢獻,在於他所創立的具特色的參悟方式——「看話禪」。所謂「看話」,指的是參究「話頭」,其中「狗子無佛性話」在《大慧語錄》中出現得最多,也是最能反映他的禪法的風格。宗杲認為要參話頭,必須將心中一切知識成見,都要通通放下,以至連能思能想的心亦要一併休歇,要以虛豁空寂的心去參究活頭。參活頭先要截斷心的思維蔔度,知解成見,是因為我們平常日用的對象性思維,一開始即以主體(能知)和客體(所知)互相分離為前提,我們的思維方式是由主體認識去把握客體,這樣做雖然可能接近,但卻永遠不能達到真理性認識,相反,只會使我們陷入思維的矛盾。他甚至認為,那些在世俗世界裏聰明靈利的人,在參禪方面的掌握,往往反而及不上那些愚鈍的人更容易找到入手處。因為這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往往是錯用心識,枉費心機,他們的知識對於生死大事是無半分交涉的。宗杲於是提出了他的看法,若要擺脫日常理性思維的束縛和控制,應該參究「無」字話頭,這不但止息了妄想顛倒,同時亦能破疑情、明根本,洞見自家心底風光。
「無」字話頭的作用
看「無」字話頭,是同時具有「止」和「作」兩方面的功用。「止」即是止息妄念思慮,達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作」即是明心見性,達到不生不滅、湛然常寂的空明境界,而且「止」和「作」的過程是一體的,止息妄念的過程同時也就是證悟清淨心地的過程。而參究「無」字話頭,關鍵是在於能參透這個「無」字即意味著破除生死心,斷絕生死命根,即是了辦生死大事。這即是說,看「無」字話頭,目的是斬斷我們慣性的分別性思維、對象性思維,使到我們在迷悶痛絕處,豁然地悟到萬法唯識,一切皆空,空亦不立的空明境界,於是就能斷分別心,滅生死心,從有分別、有對待的差別境界,進入無生無滅、無分別、無對待的涅槃境界。所以古來大德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懷疑是覺悟的前提,也是走向覺悟的門徑。在思無可思,想無可想之時,把一切思維妄想、佛法理論一齊拋卻,才能悟見光明澄徹的新天地。在這一過程中,話頭就好像一把利刃,參話頭即是以此利刃將種種虛妄、種種思量一齊斬斷,如斬一團亂絲相似,一斬一齊斬,一斷一齊斷。
使人容易起疑情的話頭,最有效的是使到我們尋常習慣的思維路數至此不再起作用,問來問去,都未得明白,反為更加迷惑,而這種迷惑正是參禪所需要的。例如,對趙州「無」字話頭,不得從「有無」的角度去尋思索解,即是不能去「思想」,而必須進入特定的禪的氛圍中去體證。「無」字在參話頭的過程中,不能做實詞解,即不能認為它有世俗所謂實在的意義,也不能認為它有聖義諦所謂實在的意義,它只具有否定的意義,作為對參禪者的警示。參禪者以「無」字,將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掃蕩盡淨,為下一步的開悟留下一空曠虛豁的心靈空間。這是「無」字的正確意義和功用。參話頭不必摒絕一切世緣,專在語言文字上下功夫,談玄談妙或做出一篇詞句美妙的偈頌,也並不是只專在靜默處去苦思冥想,只須在行住坐臥中時時照顧「無」字話頭即可。宗杲認為禪是活生生、活潑潑的,是打通了個別和一般、短暫與永恆、個體與宇宙的分別和對待之後獲致的境界。所以禪的境界只能在個體現實的生命實踐中得以實現。
第八識種子識是屬於本性或自性認識。當第八識相次不行時,即通常所說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即是意味著平素人們習以為常的分別性思維暫時休歇。宗杲認為此時正是著力處,必須著實的參究,即是將我們的原始習氣拔除,達至轉識成智,使般若之體當下即顯發無上妙用。此時已消除了我障和法障,無分別心和生死心,從而進入一種自由的天地,這就是禪師常講的自己做得主宰,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的境界。宗杲反對「說」禪、「解」禪,他認為當時禪林的頹風,皆因學人不曾親證親悟,而只在語言文字上思量計較。「禪」是了辦生死大事的生命的學問,非得親自去參證一番,不能有個悟處;沒有經歷過大疑、大死、大迷的曆練,也就不會有真實的大悟。宗杲奉勸天下學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於「生從何來,死向何去」起疑情,緊緊的把握話頭,驀直地去參,以覺悟為終極,不要懈怠,才能有直下頓了的那一刻,更要切記不可從語言知解處入手,以免貽誤一生。至於種種知見、種種語言、種種智慧,皆是末後的所得,若真正空卻本心,親證親悟到本地風光,於現實生活中應物隨緣,任他七顛八倒,皆可放曠自在,不為外境所滯礙。
「話頭禪」對後世的影響
在宋代,宗杲一生宣導的看話禪及士大夫禪學,成為叢林禪學與士大夫禪學相結合的典範。經過宗杲與其周圍士大夫的努力,禪學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而士大夫禪學也成為禪宗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禪學除了增加淨土思想及更具入世色彩外,基本上是沿襲宗杲看話禪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杲的禪學成為最後一個有創造性的禪學體系。在宗杲的生活年代,面對公案禪、文字禪的流弊日益熾盛,臨濟的宗風正在衰敗,他不能不以激烈的言詞來針砭時風,期望矯枉過正,挽回叢林的頹靡之勢。宗杲看話禪是從公案禪中脫胎出來的,與公案禪是千絲萬縷的聯繫。他並不一概的反對參究公案,因為參公案作為接引初機的方便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宗杲讓學人拈提參究趙州「無」字,他說:「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答呂舍人》卷第二八(大正四七‧九三0上))這當中公案禪與看話禪的區別在於:(1)有心參與無心參,(2)參活句與參死句,(3)親證親悟與多知多解。如所出的言句皆並非從胸襟中流出,又不是由修證而得的現量,這都是死句,而不是活句。
大慧宗杲提倡的「看話頭」,是將「敲門磚」給發心的參禪者,這深受士大夫們的歡迎。這種佛儒合流傾向,影響到宋明理學的形成。宗杲是反對弘智正覺所宣導的「默照禪」,他稱之為「邪禪」,認為是不求妙悟,只以默照。實際上「看話禪」側重在「定慧等學」中的「慧學」,而「默照禪」側重在「定學」上,兩家只是在方法上的不同。這兩家禪學,自宋以後,經元明清三代,至今仍然不絕。看話禪一直流傳到今天,現代的虛雲和尚,他是曹洞宗承傳的第四十七代,以一身而兼禪宗五宗法脈,他的禪功和苦行為現代中國禪宗傑出代表。他反覆教誨門人參禪時,要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究盡它的實質。他說:「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我們看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對「誰」這一問發起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參禪要在這有疑難的地方追究下去,看這話到底由那裡而來,是什麼的樣子,都要微微細細地去反照,去審察,這就是「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以達到反聞自性而得到開悟。參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明明諦諦的,不落昏沉,不落掉舉」,則開悟有期。他說對話頭的咬緊,就好像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處,直至不通不止,目的是「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是實在不得已的以毒攻毒的辦法。他強調參禪時最要不得的禪病就是空亡無記,坐著求靜中卻把話頭亡失了,他要我們時時刻刻,都要「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的參個究竟。他要參禪初用功的人要先認清了「主」和「客」,才能「自不為妄想遷流」,則妄想就不能成為阻礙了。當知道了下手處,就要精進猛往,切不可鬆懈,要「痛念生死,如救頭燃」,這才是修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