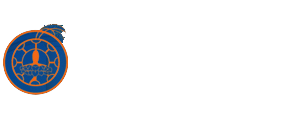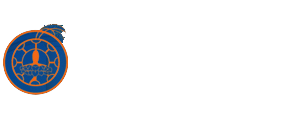代高僧支遁 ,其般若之智,适用于对真理的直觉认识,而作为真理的真实般若的道体,则是圣人的境界,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述,语言文字只是权宜假设。此即为禅宗“不立文字”思想之源头,其中亦包含《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思想。
高僧支遁的禅学思想,一方面注重以数息观为入门功夫,一方面更重视通过禅观所达到的般若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将禅由“方术”和“神异”上升为“定学”。成为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向鸠摩罗什译介的大乘禅学转变的中间环节,改变了禅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禅在社会上层的传播成为可能。
高僧支遁的日常行持,即体现出大乘菩萨对于出世、入世的完美结合。出世就是人世,烦恼就是菩提,关键在于对“幻有”世界的“真空”性把握到什么层次。这样,菩萨求佛证道,必以“世间”为依据。一方面自觉,一方面觉他。而“觉他”即普度众生,同登彼岸,则形成与小乘只求自觉,证阿罗汉果截然不同的教理风范。
同时高僧支遁禅学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道家风格,将禅与庄子的逍遥超绝和斋戒的长生成仙联系起来,不仅赋予禅以中国化的形式,使禅在中国士人和民众中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而且摆脱了印度和中国早期禅观离世苦行的特征,成为一种富于情趣的生活化的态度和行为,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在一定意义上,以后的禅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佛道渗透、佛玄交融本为魏晋时期思想环境的一大特点,就禅学而言, 高僧支遁以中国化的形式对佛教禅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通过其实践提高了禅学的地位,扩大了禅学的影响,这就是支遁禅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再者高僧支遁在学术上的价值上,则主要体现在其般若义理的方面,其涉及到万法本性以及认识这一本性的途径。因为向秀、郭象的“独化”论已经使玄学思辩无法拓展,所以,以小品《般若道行经》和大品《慧光三昧经》为中心的般若理论,继续展开对宇宙真理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既是对庄子思想的回归与超越,更是对向、郭有待逍遥观的批判,反映出支遁对自由精神的理想追述。更明确地说,支遁之所以要“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是因为其意识到,世间之学的殉俗态度及简单思维,难以达到对真理的确切把握,只有站在出世间的立场上,以智慧来思辨抽象的形而上哲学逻理,才有可能获取真理。至此,支遁以般若学为思想指导,通过参与玄学的“有无”之辨,既终结了玄学的发展道路,又超越了玄学的思维方式,一举成为代替玄学传统理论而为东晋学术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