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的“佛性論” 竺道生(355-434)。道生的佛學生涯,大約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廬山求法。第二時期,於長安隨羅什學習中觀派學說。第三時期,佛學思辨成熟期。於此時期,道生取“得意忘象”的思想方法,通過對佛教教義的獨特理解,上承諸法性空的般若之學,下開涅槃佛性之學,弘揚“法身”實有思想,他的學說都是圍繞著“法身”這一中心思想組織起來的。 在部派的毗曇學中,關於“法身”的說法,是相對於“生身”而說的。我們通稱的八相成道(由生到死的經過)乃是佛的“生身”,佛入無餘涅槃後,“生身”是沒有了,但不能說就沒有佛了,佛所證得的真理,所說的言教,即稱之為“法”的,仍然存在。有“法”在即有佛在,因此,說佛以法為身,名為“法身”。大乘對於“法身”又有了進一步的看法,在龍樹學的《大智度論》中,就有種種的解釋。大乘主張,佛既然與眾生發生交涉,同時又與各地(共十地)菩薩發生交涉,在這些交涉中佛以什麼身出現?在一般看來,佛身分“法身”與“變化身”兩種,法身是實在的,變化身是方便應化的。佛在與各種不同的人發生交涉時,根據對象的不同,是以“化身”示現的,這種“化身”是有形質還是無形質呢?“法身”是十分抽象的,“化身”應該是很具體,這兩者又怎樣聯系起來?道生根據自己學習得到的理解,寫了一系列的著作闡明了他的見解。 道生涅槃佛性論,不僅是他佛學核心思想,也是標志著中國南北朝佛學從般若學到涅槃學的轉向。道生涅槃佛性論的特點是在於“理”概念的分析。他對《涅槃經》思想的研究,首先就“涅槃”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釋,即把“涅槃”與“理”等同看待。大乘佛學的最高範疇是“理”,他認為“涅槃”就是“一理、妙理、至理”,從而以“證理、悟理、觀理”等概念,來說明對涅槃境界的把握。因為“理”是唯一的實在,所以名為“妙一之理、一乘妙理”。若把握了宇宙人生本質之“理”,所有佛教學說、思想都能一無遺漏,實現與佛的涅槃境界的相應。從般若中觀的角度探討宇宙人生的本質,通常是以“中道實相,諸法性空”為思想的出發點,即把對外部世界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建立在否定性思維的基礎上。然而,道生提出以“理”規定宇宙人生的本質,他是以一種新的觀念,即宇宙人生的本質可以從正面,以肯定的方式來表述。 此外,道生的“理”是與“佛性、涅槃”相即的範疇。道生認為,佛既是“一極”,則可與“妙一”之理對應,理就是佛,佛就是理。道生又認為,如來是佛的名號,與涅槃、佛性是同等概念。佛是“悟理之體”,所以證悟的本質,是對宇宙人生最高真實的體證、覺悟。不變之理即真實之理,是為佛所說之理,所以證理也就是證得“湛然常存”的涅槃佛性。道生說:「情不從理,謂之垢世。」道生對理與情關系的論述,用意就在於引導人們由“情”向“理”的轉化。這種觀念促使道生把“涅槃”概念與“實相”概念聯系在一起,並將涅槃學與般若學作融會調和的處理。“理”也就成為道生“闡提成佛,及頓悟成佛”的哲學基礎。 道生認為,對空極之理的體悟,必須通過般若而實現,空慧證悟空理,從般若中觀角度,觀照真理或涅槃,如同考察宇宙的真相、萬物的本質,真理或涅槃既歸於性空,又具有永恆、不變的性質,因為它們是精神性的終極存在。根據“中道”原則,“真空”與“妙有”是相互依賴的存在。空不應該是惡取空,有也不當是實有。這是說,從真理或涅槃的存在論角度看問題,它們是與現象界區別的“有”,大乘佛教所說的“常樂我淨”涅槃四德就是這一意義上的“有”。雖然它以肯定的形式表示真理和涅槃,但那是對般若之“性空”價值的肯定。因此,道生既充分利了中觀學說的成果,而又作出了若干的發展變化。道生的“妙有”仍然不是實體性,本質上與“真空”相似,都只是一般的抽象概念。但它在形式上放棄了般若空性的虛幻,通過對涅槃佛性思想的落實,找到了印度佛教中道思維與中國傳統思維的契合點。涅槃同於虛空,又是實際境界,它們並非對立的關系。對涅槃的真實境界的表述,可以推進到否定之後的肯定。“空或有”,都是對涅槃佛性的表述,只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一者否定,一者肯定。在道生看來,對涅槃(佛性)的表述,似乎以肯定方式更為適宜。肯定性的表述,並非意味著對所肯定境界的執著,若有所執著,不僅違背般若空性精神,而且有礙涅槃境界的相應。從中道實相的原理出發,煩惱即涅槃,故斷煩惱而入涅槃。所謂入涅槃度彼岸,就是觀理、見理、入理,若於現實煩惱中洞察宇宙人生的真理,便獲得真實的解脫。真理就是中道實相,觀理就是悟入中道實相。以見理為解脫的前提,包含著對真理的肯定,不可執著涅槃,則意味著肯定之否定。由此可見,道生在闡述佛性義時,雖以中觀諸法性空、中道實相原理為基礎,但結合了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的肯定表述,通過這種表述形式上的變化,將時代佛學從般若學推進到涅槃學。 佛性論是有關佛性問題的學說或理論,它的研究範圍包括:何謂佛?佛的本性是什麼?眾生能否成佛?若能成佛,依據是什麼?眾生成佛是在今生今世,還是在來生後世?成佛的方法是頓悟還是漸修?眾生成佛是依靠自力還是仰仗他力?道生把“闡提”作為人類的組成部分對待,這意味著有情眾生的成佛可能性,要高過無情之物,而闡提的成佛可能性,也要高過人類之外的眾生。傳統哲學所謂“人”的特殊地位,在道生的佛學命題中再次得到肯定。“當有”是從將來一定有成佛的結果說的,從當果講佛性應該是有。《涅槃經》就如來藏方面立說,本來就有此義,但因翻譯時,對“如來藏”這個新概念認識模糊,譯語前後不統一,意義就隱晦了。道生却能夠從中體會到說“如來藏”的用意,從而提出當果是佛,佛性當有的主張來。此外,在譯出的部分經文雖明說到“一闡提”不能成佛,但道生根據全經的基本精神來推論,“一闡提”既是有情,就終究有成佛的可能,不過由於經文傳來得不完全,所以未能見其究竟。在後來傳譯的大本《涅槃經》,果然講到了“一闡提”可以成佛。這證明了道生的預見是正確的。 “闡提成佛”的前提是“眾生佛性”,道生通過“眾生悉有佛性”的論述,把他對涅槃佛性的基本觀點清楚地展現出來。涅槃佛性論的中心議題,是有關佛性的有無、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等。“涅槃”,本意寂靜、寂滅、滅度,指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覺悟真理時的精神境界。部派佛教在理論上的發展,涅槃概念的外延不斷擴大,佛性與涅槃的平等關系逐漸確立,涅槃即佛性,或佛性即涅槃,或合稱涅槃佛性,表明了成佛範圍在不斷延伸、擴展。大乘佛教興起後,《涅槃》類和《勝鬘》類經典開始對涅槃佛性予以全面的論述。道生依據《法華經》所說“開佛知見”而展開論述。道生首先確認眾生本有佛性,這一思想實際來自《大般泥洹經》,而在上述思想中,道生體悟出佛性“本有”的內涵。“佛知見”即佛性,此是眾生“本有”的資源,只是由於煩惱所障而不得顯現。從本有說作為基礎,“頓悟”的產生才有理論的支持。所謂成佛,就是去除煩惱塵垢,而發現本有佛性。 道生“頓悟”說的主要理論依據是“理不可分”思想。“理”,在道生的佛學體系中,相當於涅槃、佛性、法身、法性等概念,是宇宙的最高真理,也是學佛者要證悟的唯一實在。既然真理是玄妙整體,對真理的證悟必然是一次性的整體完成,這就是所謂“冥符、契合”。頓悟不是主客體對待的認識問題,而是指達到涅槃境界的神秘直覺。“智”是直覺主體的特殊智慧。“理”是智慧所要證悟的對象。真正的頓悟是要在對“理智”全然排除的情況下實現,這就是道生所說的對“湛然常照”之真理的冥符。道生“頓悟成佛”說的又一重要內容是“積學無限”和“不廢漸悟”。道生,他一方面主張“寂鑒微妙,不容階級”(指頓悟);另一方面又認為“積學無限,何為自絕”(指漸悟,包括漸修)。可見,道生在強調頓悟理念的情況下,也不放棄漸悟的理念。道生的“頓悟成佛”說,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寫下重要一頁,是對傳統佛教思想,以及修養方式的一次有力沖擊。 道生的涅槃佛性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獲得空前的特殊地位。這主要由於“涅槃佛性”所談論的對象及其內容,不僅與中國傳統人性理論具有可比性、類似性,而且還能彌補傳統人性論,在形上學哲學思辨方面的不足。道生對涅槃佛性問題的興趣,顯然與傳統人性問題討論相關,是要在般若學思辨的基礎上,將理論的重心轉移和落實到人的本質問題上,形成對人生根本問題的共識。由此可見,道生的涅槃佛性論,不僅揭開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而且對學術界的影響是極其深遠。 參考資料:呂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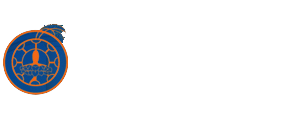 |
E-Learning Programs |
||||||
|
|||||||
|
|
顿悟 及 一阐提
道生虽然集般若、涅盘、毗昙于一身,但却以“涅盘圣”传扬当时、后世,其学说以佛性为根据,以成佛为核心,对中国佛教心性哲学建设的突出贡献就是上述“本有于当”的正因佛性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方法论——顿悟,和一阐提人皆能成佛的“应有缘”论。如是,在佛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做出了新的贡献——调和“本有”和“缘生”。
1.顿悟
顿渐之辨虽不始于道生,但道生因主大顿悟而彪炳史册。
据南齐刘虬《无量义经序》,顿悟之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乃支遁,安即道安。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云:“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可见,顿悟之说始于支道林。
十地亦称十住,菩萨进修,必循十住,即由初欢喜地,至十法云地。第七远行地,为十住中的特殊阶段。中心意思就是说,修行只要达到第七地,便可以“圆照一切,诸结顿断,即得佛之摩诃般若,即于此而有顿悟。”简单地说就是,至于第七个阶段,便可顿悟。这就是通常说的小顿悟。主张七地顿悟者尚有僧肇、慧远,法瑶等。
总而言之,顿悟是一时之悟、整体之悟、不容阶级、不借言语之悟,当然也是自悟。如是,“《般若》无相义,经生公之精思,与《涅盘》心性之理契合,而成为一有名之学说。”以后中国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成佛论便是以此说为理论基础,以顿悟说风靡于世的,只不过“识得本心,便能成佛”,远比道生的顿悟论更为简易直截罢了。
2.一阐提有性与应有缘义
既然佛性本有,而且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人(善根断尽之人)也当有佛性,也可成佛。这是道生的佛性论最具挑战性的命题,也是备受责难的观点。
一阐提,梵文Icchantika之音译,亦译“一阐提迦”等,意为不具信、断善根。佛经谓其“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也就是无可救药之人。早期传人的六卷本《泥洹》无阐提有性并成佛说,是同大《涅盘经》的显著差别。六卷本《泥洹》卷三云:
如一阐提懈怠懒惰,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
而大《涅盘经》北本卷五于同处增改为:
如一阐提,究竟不移,犯重禁,不成佛道,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尔时便灭一阐提。若复得作优婆塞者,亦得断灭。于一阐提犯重禁者,灭此罪已,则得成佛。
又如《泥洹》卷四,虽然说众生皆有佛性,但特别强调一阐提除外。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
当然还有,不再列举。总之,早期(东晋末年)所传六卷本《泥洹》为法显所得,与北凉昙无谶所以四十卷本《涅盘经》(北本),以及后来由慧严、慧观和谢灵运改变润色的三十六卷本(南本)有诸多不同。应当说六卷本实未窥涅盘经义之全豹。道生孤独发明,依义不依文,从逻辑上说明,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若为众生,一阐提固有佛性;并且大胆断言《泥洹》未必尽善,自然不足为据,也可以看出道生在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敢于标新理、立异义的开拓精神。他说:“禅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传度未尽耳。”“一阐提者,不具信根,虽断善犹有佛性事”。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既然一阐提必有佛性,那么按照逻辑推论,包括一阐提在内的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如此何用修道?又何以做如是艰难的理论说明?“譬如七人浴恒河中,而有没有出,则因习浮与不习浮也。故众生成佛,必须借缘”。换句话说,众生虽有佛性为成佛之因,但仍需有缘,即有条件方能成佛。这就是道生的“应有缘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成佛论。如此不仅弥合了一阐提有无佛性的冲突,同时也以佛教“缘生”的基本理论,消除了涅盘实相、佛性实有和般若性空的悖论。
为了说明成佛的有条件性,即“应有缘”,道生又提出了“心”和“智”这两个概念,强调成佛必借助“心”“智”。在这里,心、智仅仅是作为“缘”(条件)而同佛性相互呼应的。另外,一阐提虽断善根,但却是爱欲之结晶,梵文亦为“一遮案提”。“一遮”为贪欲,“案提”为鹄的,即以贪欲为唯一鹄的之人。既然“苦处”、“爱欲”、“善法”皆为“缘”(条件),那么一阐提则借爱欲之恶缘感佛,圣人再依缘起智,以心相应,一阐提成佛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此说,固然艰涩,但总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众生成佛,必借因缘。一阐提若得佛智之应化,自然能够成就无上正觉。佛性论同缘生论相互印证,应当说也是道生思辨哲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