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子对墨子墨家的批评,如无父、禽兽之道等,已为人所知。对于孟子的评论,我们需要考量当时儒墨两家在论战时的语境。故由《论语》和《孟子》中所涉“亲亲相为隐”以及墨家典外文献《吕氏春秋》(杂家)记录的墨家巨子杀子奉法的案例,我试分析墨家是否真的是“无父”和弃绝血缘关系。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儒家言说传统下,除了犯上作乱等“十恶不赦”大罪外,亲属犯法是需要匿罪容隐的。“亲亲相为隐”一直被标榜为儒家五伦之内血亲情理外扩为治法公领域层面的道德基础,与之相对的“大义灭亲”似乎就成了天然的“政治不正确”。因此回顾古代中国一位墨者父亲的杀子公案,尤其有意味。 “墨家巨子”杀子能说明墨家蔑视人伦、冷酷无情吗?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非墨者独有 墨家典外文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了一则巨子(亦称钜子)腹䵍“大义灭亲”的事例。 “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私》)” 先秦墨家由于高扬“兼爱”,而被孟子批判为“无父”、“禽兽”。相应地,“腹䵍杀子”,也被后世儒生用以支持墨家大公无私以至于缺乏五伦之内血亲伦理等观点。“腹䵍杀子”虽然归属墨学典外文献,非在《墨子》53篇和墨学十论义理之内,不过其所述墨者之法和墨家组织形态与墨学文本和墨家历史相符。因而,有必要再次探讨“辟墨”儒生所举证的“腹䵍杀子”,是否能坐实墨家蔑视人伦、冷酷无情、禽兽不如的观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经典文献或者历代法条判例,既有包含“亲亲相隐”精神的容隐观,也不乏鼓励大义灭亲的因素(从经典文献,到法条判例,甚至民间的小说传奇,都有激赏“大义灭亲”的例子)。所以,问题的根源不是去分析哪种文化有没有血亲伦理,而是去分析该文化所保守的血亲伦理在何种处境和条件下,能够将之致以大义灭亲的地步——即在判断选择路径时,由血亲伦理出发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还是另有一个高于它的价值(行天下之大义的“兼爱”)在指导。 其实,“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并非墨者之法独有,相关论述在先秦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官》);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若考察《墨子》文本,更会发现巨子“大义灭亲”的举动,似乎也构不成墨家“大公无私”的无血亲伦理的指控。《墨子》全书未见无私表述,倒是有“虽上世至圣必蓄私”“天下之利欢”(《墨子.辞过》)的记载。《墨子》全文除了使用“王公大人”一词外,“公”字仅出现一次——“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即公义应该取同自百姓,用于辟除人们的私怨。 腹䵍杀子能说明墨家蔑视人伦、冷酷无情吗? 腹䵍的做法体现墨家的“法无偏私” 《吕氏春秋》高度赞赏腹䵍杀子奉法的行为——“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儿子是人们所珍爱的,忍心割舍自己所真爱的血缘亲情而去推行普天之下的大义,墨家巨子腹䵍可谓真正的“大公无私”)。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腹䵍违背血亲伦理的杀子举动呢?特别是在秦王应允特赦的情况下还如此行? “子,人之所私也”,血亲情理是人人珍视的;但是“忍所私以行大义”以至杀子,那么被置于血亲情理之上的因素是什么? 从原典义理出发,我认为: 第一,《墨子.尚同》篇说“信身从事”,墨家认为一个法律在君王自己也遵守之后,才会成为有效的法律。所以腹䵍的行私刑恰是行公义,而秦王的特赦恰是破坏公义;第二,墨家认为王公大人是“天下器”(《墨子.亲士》,必须守法,“以身戴行”,否则就不是兼王之道,不能“兴天下之利”。也就是说对于墨家而言,如果有什么价值置于血亲伦理之上,以至于违反亲亲相隐而大义灭亲,那就是“利爱”——即“兼爱”的最高原则。 若从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视角去评价墨者的“大义灭亲”行为,十分容易出偏。按照儒家的推恩说,孔孟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又怎么会珍惜亲人的生命呢?没有亲情的百姓更不在话下。儒家阐释孔子《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全部有赞赏“大义灭亲”内容。而腹䵍儿子这个案子法律要惩治他儿子在前,秦王徇私情问巨子要不要对他儿子法外开恩在后。秦王违法要放过他儿子,他不接受罢了。 接受秦王罔法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接受特赦以后,墨家恐怕要臣服于秦王了。这对墨家的独立性是毁灭性打击。墨者可以个人身份任官,成为家臣(当时所有官员都是家臣身份),巨子则不能在该国不实行“墨者之法”的情况下任官。墨子不接受越国封地的时候就说:实行我的主张,我不要封地;不实行我的主张,我去任官是出卖了“义”——墨者之法。 巨子腹䵍坚持墨家法治主张,不出卖自己和墨家学派,是十分伟大的行为。若将“法”概念扩大为“义”,称为“大义灭亲”,再批“大义灭亲”中过分的内容,就存在概念偷换问题。腹䵍的做法顶多能称为墨家主张的“法无偏私”。 因为,墨家在儒家血亲情理之上,尚悬置一个高于五伦的transcendental principle,即行天下之大义的“兼爱”价值所在。 《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可作比较 类似“腹䵍杀子”的情况也出现在神本宗教的伦理辩难问题中。基督教《圣经》文本中就包含不少“大义灭亲”的例子,如著名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此可以有个比较。 “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圣经.旧约.创世纪22:9-10》)” 神本宗教中,当血亲关系与宗教信仰相互抵触时,人对特定他者(上主)的委身似乎是绝对的,亦即这个绝对义务与伦理性的责任似乎不可通约。存在主义之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就暗示,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正是由于他以一种信仰的激情来完成对血亲关系的“无限的弃绝”,并且可以在置于道德两难的处境下把谋杀儿子的卑鄙行为变成上帝悦纳的献祭举动。 相反,我们会发现类似的表述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比较少见。 李泽厚先生认为尽管儒家也有斩断人伦情爱的案例,但是如儒家宣讲的大义灭亲、郭巨埋儿之类,它们不但世俗的条件性、相对性极强,而且也远非核心观念;在原典儒学中,孟子倡导的是舜负父出奔即孝大于忠,亲情高于王位甚至律法。因此,如果从大义灭亲的向度来反观亲亲相隐,还是能够发现儒家伦理思想中较少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而达到圣爱或者兼爱的超血亲伦理境界。 不能将“无父”、“禽兽”恶名冠于先秦墨者头上 而当我们反观儒家言说传统下,孔子告子路“亲亲相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以及孟子论舜的两个案例“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似乎确有将实践果效上不义的行为作为一种“亲亲为大”之美德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处理公德公法公领域和日用人伦私领域的混淆。 亲亲相隐或者大义灭亲,是考验血亲伦理是否具备普适性以及由其所推演的利他行为如何可能的高峰议题以及矛盾焦点所在,历来在汉语学界关于儒家血亲伦理的争鸣有很多,除了从儒家血亲伦理本身发出的回应外,亦有从柏拉图《游叙弗洛篇》游叙利弗洛证父杀人以及罗马自然法判例中的“容隐制”的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的。常规上的伦理辩证往往走向了“忠孝—血亲伦理—亲亲相隐”与“仁义—普世价值—大义灭亲”二者必取其一的简单二分,容易产生过度诠释和处境错置。 邓晓芒先生认为,即便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为亲属隐罪的观念,亦不能证明为亲属隐罪或损人利己就是天下公义。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这一弱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容忍这种弱点;与将之鼓吹为一种优点,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普世文化而言,血亲伦理天然内蕴于各大宗教文化当中,从血亲伦理出发的亲亲相隐,亦是人之常情,不独以儒家为特殊。同样,既然亲亲相隐之于普世宗教文化并不具备特殊性,那么大义灭亲也一样不具备特殊性,自然也不能因之将“无父”、“禽兽”的恶名冠在先秦墨者头上。 因此比之儒家言说传统下“亲亲相为隐”无限扩展导致的“任人唯亲”、“血亲腐败”,墨家巨子腹䵍杀子奉法的“大义灭亲”,反而多了几分对法治精神的坚守,不但不应该给予责难,反而是要大力高举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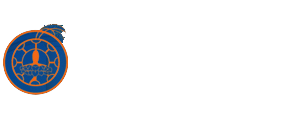 |
E-Learning Programs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