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者與去法,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中論‧觀因緣品》所探討的是“生”的問題,而〈觀去來品〉所觀察的是“滅去”的問題。〈觀去來品〉所討論的,側重在否定實有自性者的運動論。運動,在時間空間中活動,從此去彼,從彼來此,就名為去來。去來,不單就人說,一切法在空間中有位置的移動,也就稱之為去來。就是在時間的演變中,有性質,分量,作用的變化,從過去來現在,從現在去未來,或者從未來來現在,從現在到過去,都是去來所攝。說到徹底處,生滅就是去來。諸行無常的生滅法,是緣起的存在,存在者,就是運動者,沒有不是去來的。不過,一般人受著自性見的欺誑,不願接受一切法不生的正見,他們以為現實的一切我法,眼見有來去的活動,從相續長時的移動,推論到剎那間也有作用的來去,有來去,就不能說沒有生滅。所以他們要建立來去,用來去成立諸法有生。 印順導師認為《中論》是闡述《阿含經》佛說緣起的深義。八不之首是「不生不滅」,〈觀因緣品〉是說明觀集不生;「不來不去」是八不之終,〈觀去來品〉判為觀滅不去。也可以說,〈觀因緣品〉總觀諸法的無生滅用,〈觀去來品〉總觀眾生無來去用。前品去法執,後品除我執。執著諸法有真實自性的,如果觀察他自性來去的運動,就明白運動是不可能的。但緣起的來去,不能否認,所以自性有的見解,是虛妄的。世間的智者,見到人有生老病死的演變,世界有滄桑的變化,也有推論到一切一切,無時不在生滅變化中的。但一旦發覺他本身的矛盾,就從運動講到不動上去。的確,執有實在的自性,運動是不可能的,除非承認他本身的矛盾不通。譬如從這裡到那裡,中間有一相當的距離,在此在彼,自然不是同時的。這樣,空間的距離,時間的距離,不妨分割為若干部分,一直分割到最後的單位,就是時間與空間上不可再分割的點。從這一點一點上看,在此就在此,在彼就在彼,並沒有從這邊移轉到那邊去的可能。如果有從此到彼,這還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在現象上看,雖似乎是運動,有來去,但就諸法真實的自體上看,運動不可能。我們所見到的活動,是假相,不是真常的實體。 佛法的根本見解,諸行無常是法印,是世間的實相,就是諸法剎那剎那都在動,一剎那都是有生也有滅,沒有一刻停止過。佛法中,像三世實有派的一切有部,他雖也說諸行無常,但無常是約諸法作用的起滅,而法體是三世一如,從來沒有差別。可說是用動而體靜的。現在實有派的經部,不能不建立長時的生滅,假名相續的來去。也有建立剎那生滅的,但一剎那的生滅同時,與前後剎那的前滅後生,中無間隔,是含有矛盾的。所以不能從一切法性空中,達到徹底的諸行無常論。無自性的緣起假名有,是動的,不是真常的,所以說無常;無有常,而卻不是斷滅的。從無性的緣起上說,動靜相待而不相離。 〈觀去來品〉,從先後上觀察,已去和未去都沒有動作的現象,去時即半已去、半未去,仍然是離不開已去和未去,而且,時間不離動作而存在,去時是不離去法而存在的,從無自性的緣起論,已去、未去、去時三時中,實有自性的去法是不可得的。但是,實有論者仍不放棄,說離了動作沒有去時,這是對的,但去時去還是可以成立。這因為有去,所以能成立去時,就在這去時中有去。雖然,執著實有者,論理是不能承認矛盾,而事實上卻無法避免。所以進一步的評破:若固執去時有去,則應有二種的「去」:一是因去法而有去時的這個去(去在時先);二是去時中動作的那個去(去在時後)。一切是觀待的假名,因果是不異而交涉的。因去有去時,也就待去時有去,假名的緣起是這樣的。但執著自性的人,把去法與去時,看成各別的實體,因之,由去而成立去時的去,在去時之前;去時中去的去,卻在去時之後。不見緣起無礙的正義,主張去時去,結果,犯了二去的過失。有兩種去,又有什麼過失呢?這犯了二人的過失,因為去法是離不了去者的。去者是我的異名;如我能見東西,說是見者;做什麼事,說是作者;走動的,說是去者。佛教雖說緣起無我,但只是沒有自性的實我,中觀家的見解,世俗諦中是有假名我的。我與法是互相依待而存在的。凡是一個有情,必然現起種種的相用,這種種,像五蘊、六處等,就是假名的一切法。種種法是和合統一的,不礙差別的統一,就是假名的補特伽羅。假名我與假名法,非一非異的,相依相待而存在。所以去者與去法,二者是不容分離的,有去法就有去者,有去者也就有去法。這樣,若如外人的妄執,承認有二去法,豈不是等於承認有二去者嗎?要知道:離於去者,去法是不可得的。所以,龍樹直從去者的待緣而有,掃除去者的妄執。龍樹又說,假使有去者,也仍然不能有動作的去。因為要有去,就不外是去的那個人在那裡去,或者沒有去的那個人往那裡去。去的那個人能夠有去的動作,一般都看為是的,其實去者就是已經去的人,動作也過去了,那裡可說去者還有去呢?所以去者不去。至於不去者,當然也不能有去的動作,因為不去,就等於沒有動作。去者,不去者,都不能去,或者以為有第三者能去,但是這第三者,不是去了,就是沒有去,所以,離了去者與不去者,根本沒有第三去者的存在,所以第三者去,同樣的不可能。 再從體性是一是異上說,假使說去法就是去者,是一體相即的,就犯了作者及作業,是事為一的過失。假定說去法有異於去者,去者與去法,是條然別異的,這就犯了二者可以分離的過失。去是去,去者是去者,彼此互不相干,沒有任何的關係。那就應該離去者而有去法,離去法而有去者了。然而,依正確的因緣義說,去法與去者,都沒有固定性,是緣起相待的存在;彼此是不一不異,非前非後,非一時的。在不觀察的世俗諦中,因此有彼,因彼有此,去者與去法都成立。如果一一看為實有性,那就不是一就是異,不是先就是後,必然的陷於拘礙不通之中。 從上面種種的討論中,去法,去者,及所去的處所,皆無自性,唯是如幻的緣起。〈觀去來品〉,從來去的運動中,推論到人、法、時、處都沒有決定的自性,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依相待,不一不異的,顯示出一切無自性的緣起。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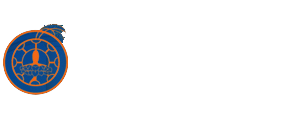 |
E-Learning Programs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