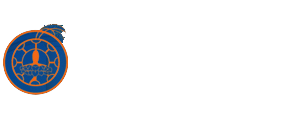对于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时代,为了明哲保身,人们流于清谈,“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成为玄学的前身。时代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减少,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汉代儒家经学研究,道家清淡无为思想因此而被重新发掘。同时,人们也不再迷信汉代那考证繁琐、甚于谶纬的经学,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此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等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论著提出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或为政治原则寻找理论依据。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独立并进行自觉创造的时代中,产生了魏晋玄学这种后起于经学,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学。
首先是因为汉魏易代之时经学衰落,人们思想领域动荡而急需他种学说或思想来填补精神空白。汉代时期阐释经学成为学术主流,但这种对经学的过度追捧本身存在很大问题。一是经学研究的古板化。汉代学者局限于儒家经典章句而不能从更广阔的领域中阐发,尤其忽略了经典本身传递出的内在思想性特征。一是经学作为一种思潮性学术研究,成为了统治者统治社会的思想外衣。但是在汉末,随着统治阶层的混乱与崩溃,作为统治工具的经学也受到冲击并一蹶不振。其次是在动荡的社会中清谈风气的兴起。曹魏时代,用人举士唯才是用。这种选人标准在曹操的《求贤令》(《全三国文》)中可见一般。
曹操采用刑名法术之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笼络人才,但直接后果便是社会道德支柱被破坏。到司马氏统治天下时,人物品评之风转向了谈玄论虚。清谈所讨论的问题,贺昌群先生认为“发引于新旧经解之问题”[3](P61),已经大致可以看出与后来玄学相关的宇宙本体、圣人之情等主题。第三是先秦道家思想在魏晋时代的延续与发展。自先秦时代起,儒家与道家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经历过动乱的春秋战国来到统一的大汉时,儒家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大汉将尽之时,儒家的名教被统治阶级异化变成维护统治、残害人们的工具。于是,道家斗争之风再次兴起,只不过,此时的学者并不是对老庄道路的单纯复制,而是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思考。
在魏晋玄学中,由于“名教”与“自然”的概念范畴不同,导致了玄学家们产生了对其或支持,或反对,或融合的发展观。
裴頠是一位典型的“名教”支持者。在裴頠看来,“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无”是空虚的,什么都没有,不仅不能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更无法指导人们的现世行为。虽然在《崇有论》中,裴頠一再从批判“贵无”派的不足入手,如“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实践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世间万事万物都为“有”所生,而此“有”在实际上又指代了现实的政治与礼法制度,也就是“名教”,且所指的是“名教”范畴中的“真名教”,因此,我们应该尊崇此“名教”下的规则,各司其职。所以,裴頠认为,当作为本源的“有”产生了万物之后,也就是我们应该在现实之中尊崇名教的时候。在名教的发展观上,裴頠是积极的支持者。
嵇康是一位典型的“名教”反对者。在《释私论》一开始,嵇康就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正因为嵇康在自己的遭遇和周围人的境遇中看到了“伪名教”,也就是司马氏所利用的、被异化了的“名教”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所以在“名教”发展问题上激烈地主张“越名教”,也就是放弃人为的“措”,放弃非自然之性的“矜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内心和性情。
王弼是一位支持与反对的融合者,因为在他的体系中,既主张“崇本息末”又主张“崇本举末”。“崇本”即以“无”为本,以“自然”为本。但为什么会有“息末”与“举末”之分呢?很明显,王弼之所以持这样的发展观,正如在概念范畴上的分析,原因就在于此处的“末”有不同的意义。在“崇本举末”中,“末”代表的是“真名教”。而在“崇本息末”中,“末”指的是“伪名教”。因为王弼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论述自己的“有无之辩”的,所以在现实发展层面上就更理想化。但无论是“崇本息末”还是“崇本举末”,王弼都是用一种“体用如一”观进行融合。所以在方法论上王弼产生反对“伪名教”和支持“真名教”两种态度,形成融合派,且是在哲学上的融合。
郭象眼中的万物是“独化”、“自生”的,《庄子•大宗师》注曰:
无也,岂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则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宇宙万物自生,名教也如此。名教本身既然已经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名教的发展问题上当然应该“自然地”尊崇名教。总观郭象的态度,是顺应自然性的名教,也是融合了名教与自然,是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真正融合。
从思想上说,魏晋玄学家通过对宇宙本体等问题的探讨,将儒道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思考做出了自己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