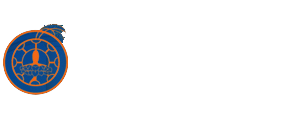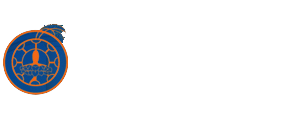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
作为文人,阮籍、嵇康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从司马氏策划政变,由高平陵事件到嵇康被杀的过程当中,无数文人士子被莫名其妙的卷入权利斗争之中,成为阴谋杀夺和集团利益的牺牲品。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正是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他们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了威胁,从而导致了他们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和精神上的失落。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和人格信念的重新构建,阮籍、嵇康借诗文创作来抒写对时政的不满,抒发个人对时代的怨愤,同时他们又在现实生活中做出一些越礼悖教、惊世骇俗的举动。
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们反抗时代和统治者的勇气、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诗性才情和风度。他们的人格魅力又与其诗文创作是紧密相联的,诗文创作印证和折射了阮籍﹑嵇康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们对待司马氏政权采取了不同的反抗方式,诗文风格也有所差异,最终的结局也不同,但他们诗文创作达到了“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2]的境界,他们对生命和时代的反思又使我们看到了魏晋文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寻。
阮籍﹑嵇康在当时来说都是标准的美男子,他们志向高远,博学多才,喜好老庄哲学,能弹琴、善饮酒、好作诗,但又显得荒诞不羁,在生活中常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一)阮籍的人格魅力:
关于阮籍,首先他最大的魅力在于借醉酒处世。阮籍的醉酒同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时代氛围有密切联系。但当他面对自己所处的严酷环境时,阮籍便立刻转向醉酒了。阮籍是一个对现实洞察力极深的人,他明白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尽管内心充满了郁闷和不平,但他又缺乏嵇康那种直面现实、公开反抗统治者的勇气,所以他不得不对当权者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以醉酒的方式来超脱现实,掩饰自己内心的真正意图。从阮籍的醉酒中我们发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一般人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而阮籍喝酒醉酒则饱含了一种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尽管他的这种态度有几分狡黠和圆滑,但的确富有魅力,不失为乱世文人避世存身的一种良好方式。阮籍既能借醉酒来反抗统治者,又能做到出言谨慎,这无疑需要超人的心灵厉炼和胸怀。这种智慧和定立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换了普通人或许只是单纯的喝酒,醉酒后恐怕又会胡言乱语或是酒后吐真言了。
其次,阮籍的人格魅力在于他以怪诞的行为回避出仕。古代士人都有济世报国的政治理想,而阮籍在政治上则采取了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态度。即使后来出仕也与当权者虚于应付、敷衍了事。阮籍面对当时的司马氏政权的黑暗和血腥,他无力挽回正常的统治秩序,只能为时世担忧而内心痛苦。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在他极度苦闷的时候,往往“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而返”[13。与嵇康相比,他的这种反抗统治者的方式既保全了自己,又以圆润﹑通达,超脱的处世哲学为后代乱世文人提供了借鉴。
(二)嵇康的人格魅力 第一,为人正直,直性侠中,刚肠嫉恶。嵇康在性格上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敢于正面同当权者进行斗争的勇气和骨气。
第二,嵇康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不畏当权者和最高统治者,敢于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主张。在当时那样一个黑暗恐怖的时代,许多文人都惟恐避祸不及,而嵇康竟然敢得罪当权者,这无疑需要超越常人的思想和勇气。。在司马氏的严酷统治下,文人在政治上大多是失意的,而虚伪的名教和专治统治又束缚了他们的身心,文人因此想通过老庄放达无为的思想来亲近自然,以忘却政治上的失意,寻找情感上的安慰寄托,并籍以保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摆脱外物的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但当时并没有人敢从理论上构筑一种思想来彻底否定司马氏的名教,嵇康却这样做了。他为了平衡心中理想与污浊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为了对抗虚伪的名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从根本上触及到了司马氏在政治上利用礼教进行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与阮籍越礼悖教又顺乎人情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为此,他还极力崇尚自然、清谈玄远,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率而相携,啸傲山林,极浪游之势,借以放纵自己的身心,实践了“任自然”的主张;为了从根本上进一步揭露司马氏礼教的虚伪,他在《绝交书》中更宣称自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了作官的七不堪、二不可,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昭极为愤怒。此时恰好嵇康因吕安事件而受到牵涉,司马昭便听从了贵公子钟会的诬告借机杀了嵇康。由此可见,嵇康的死是必然的,他危机了统治者的利益必然要受到统治者的惩处。嵇康敢于得罪贵公子钟会,敢于得罪最高统治者司马昭,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主张,既根源于他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又表现出了他“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高尚气节。
第三,嵇康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文人的风度。魏晋风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给人很直观的印象是:宽袍大袖、弹琴饮酒、吟啸赋诗、思辨自适、诗性才情、贵族士大夫的气质风貌、人格的高傲不羁等。嵇康作为魏晋文人,他饮酒赋诗,无论人格、才学、品貌自然是无人能及的,前文中已提到。他有士大夫的贵族风范,又有打铁的特殊嗜好。同时,嵇康对老庄哲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以其卓越的才学,名士的风度,活跃于太学辨论讲坛,投身批评王肃(司马昭妻父)的太学辩难活动之中,在太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诸多的名流鸿儒望尘莫及,以至于嵇康被杀时,竟有“太学生三千上书,请以为师”[23]。嵇康的气度也是超凡的,当他临刑东市,面对着众多的太学生和送行的人群,“康顾视日影,视气不变,索琴而弹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24]嵇康面对死,却流露出这样坦然的气度,他不为自己将要被夺去的生命而伤悲,却仅仅为一首《广陵散》的失传而感到遗憾,这不能不让我们受到心灵的震撼。也许正是《广陵散》使嵇康的魅力和魏晋风度化为正始之音绵绵流淌而不止。嵇康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风度和精神是不朽的,《广陵散》的琴音,也正是他高尚的人格和品行的一种升华,更是魏晋士人精神风度的又一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