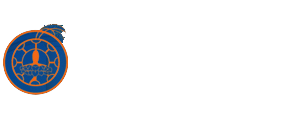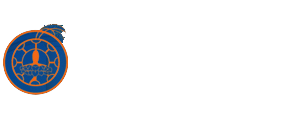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一) “文”“质”结合,保留原作文体风格
中国佛经翻译的两个主要方法是“文”与“质”,“质”既质直,也就是直译,而“文”则是意译。译经过于“质朴”和过于“文丽”都会影响佛经要义的传达,但是“质”和“文”并不是对立的,因此虽然鸠摩罗什的翻译倾向于意译,但是其翻译技巧娴熟,能够很好地将“文”和“质”统一,既不过于“质朴”也不过于“文丽”。他认为,佛经翻译在达旨的同时语言表达要简洁优美并且符合汉语读者的言语习惯,使佛教徒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译经。罗什曾与僧睿讨论西方辞体时,说道:“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就是说,西域梵文经文辞体华美,可作歌词吟唱,但被译为汉语后,虽然能保存原文大意,却与原文的文体大相径庭,失去了原文语言的美感。罗什门下四大名僧之一僧肇在《百论序》中提到:“与什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力求译经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保留原文的异域语趣并采用符合汉语习惯的简洁精炼的文字表达进行传译。他有许多经典译作,其中《金刚经》以及《法华经》影响最大,他的译本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可读性强,在文学境界上,是后来玄奘等译者无法超越的。 (二)音译专有名词,增添异域情趣
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者经常采用“格义”的方法翻译佛学概念,导致译文晦涩难懂,罗什完全摒弃了“格义”的方法,对于佛学中的专有名词、专用术语及在汉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表达的梵文词汇,他都采用音译法,并力求统一译名,避免一词多义的现象,使译文忠于原作,易于读者理解,同时也保留了异域文化色彩,增添了文字的美感。如在《金刚经》的原文本中称呼释迦牟尼的词语很多,罗什将其统一翻译为“世尊”和“佛”。又如“菩萨”、“欢喜”、“神通”、“清净”、“极乐”、“菩提”、“舍利”、“罗刹”、“涅��”等词,都是罗什根据原作创立和音译出来的。这些音译词翻译了佛教概念并体现佛经翻译的新思想,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丰富了汉语词汇,使译经更加忠实于原作,避免了读者理解上的分歧,增添了异国色彩,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态度严谨,下笔慎重
罗什在翻译佛经时,先将梵文经文口译成汉语,讲出义旨,经过译场中几百个人详细商讨并对照旧译后,才形成初稿。然后再讨论校正、复校,确定用字准确,行文流畅,才作定本。罗什本人对翻译工作认真负责,加上译场中有僧睿、僧肇等名僧相助,出现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时,众人辩论商榷,“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正如他在翻译《十住经》时,“一月余日,疑难犹豫,沿未操笔”。直到与他的老师佛陀耶舍商讨并理解经义后,才开始动笔翻译。
梵经中咏叹吟唱的部分较多,大多重复,若全部将其译为汉语则显得繁重哕唆,为了使佛教信徒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经的内容,有助于讲经、读经和诵经,罗什删去了梵经中重复繁重的内容,使译经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及音律特点。胡适曾说到:“后人讥罗什译经颇多删节,殊不知我们正惜他删节的太少。印度人著书最多繁复,正要有识者痛加删节,方才可读。”然而,“什译虽多剪裁,还极矜慎”,据僧睿记载,罗什译《大品般若》时“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故异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由此可见,罗什对待译经工作认真严谨,经过反复的商讨和对比梵文原作和汉语表达后才作出删减的决策。
罗什发现以前的经译存在“义多纰缪,皆由先度失旨,不与胡本相应”的问题,因此他对一些佛经进行了重译。虽然从道安开始重译旧的译经,但罗什精通梵语,又懂汉语,因此他能更准确地发现旧译中的纰缪,再加上僧睿、僧佑、僧肇等人辅助其翻译及校正,保证了罗什重译旧经的质量。此外,为了对所译佛经负责,罗什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译者署名的译者。
(四)组织译场,分工负责
最初的佛经翻译是私人活动,一般由来自异域的僧人背诵佛经,译者将经文口译为汉语,另外一人把译成的汉语经文记录下来,最后进行修改。罗什被姚兴接至长安后,开始组织译场,参加翻译的人数大量增加,而且分工明细。例如,翻译《大智度轮》时,有五百人参与;《思益经》的翻译则有两千余人参加。其中,一大部分人是来听经义,参加辩论的。除了译主口译经文外,其他程序可由多个人共同完成,整个翻译程序则包括口译、记录、考正和校对等。经过集体商议和讨论,所译佛经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有人认为,罗什的译经,不论在技巧的熟练运用方面,还是在内容的正确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