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談老子「道」之六義。 唐君毅先生運用字義類析的方法談老子「道」之六義,並且以虛實的判斷出形上實體之道是貫通六義的起點,由此而主張老子之道是一客觀的實有。「道」之六義分別是:(1)貫通異理之道,(2)形上實體之道,(3)道相之道,(4)同德之道,(5)修德或生活之道,(6)作為事物及人格心境狀態之道。 (1)貫通異理之道 萬物各異理,說明物物各有它不同之理。所謂道盡稽萬物之理,即說明道遍於萬物的異理,有通貫一切異理的功用。道的第一義:通貫萬物的普遍共同之理,或自然或宇宙的一般律則或根本原理。所謂萬物的共同之理,並不是實體,而可以只是一虛理。所謂虛理的虛,即表顯狀似理的自身,而並無單獨的存在性,雖然是作為事物的所依循或所表現,而並不可以視為一個存在的實體。道的意義可以從道這個字的字義來說明,即人所行道路引申而來。初時固然只是一行為的方式,並非存在的實體,只是附屬於人的存在的實體,而不能離人的自身而存在。道家所說的天地萬物之道的一義,就是天地萬物之所依循而行,而並不是一個存在的實體之義。如果認為這道之義,等同於萬物共同之理,或自然律則,宇宙原理,則它作為理或律則,亦只是虛理和虛律,而並沒有它自身能夠實際的存在。《老子》七十七章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這規律形式,簡單的說,即是「凡極必反」,故此以張弓的形式來作比喻。這凡極必反,亦即是道家與陰陽家及易傳,所共同最重視的萬物的共理,或普遍的自然律。老子是首先提出重視這自然律的必然性。 (2)形上實體之道 老子「道」的第二義明顯的指出一實有的存在者,或一形而上的存在的實體或實理者。這第二義與前述的第一義之道只是萬物的共理,或普遍的自然律,它們的分別是在於一虛一實。所謂虛者,是說它本身不能單獨的存在,沒有實在的作用,也沒有實在的相狀。所謂實者,是說它本身有實在的作用和實在的相狀的真實存在的實體或實理。這第二義之道,是老子的形而上學中最為重視的一義。《老子》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說明了「道」是一形而上的存在者,有生起萬物的實在作用。這有生物成物的實在作用的形而上道,並非孔子、孟子、荀子學說中所說的「有」。《中庸》說:「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意思是,天地的道理,因為有「誠」主宰其中,所以能化育萬物,深不可測。這樣的天之道,才可視為形而上的生物者。 (3)道相之道 道相是道體對應萬物而呈現的相狀,它的意義本來就與道體有分別。然而,因為道相依據於道體,而「道」這個詞語,是可以專指道體,亦可同時指為道相,這就是第三義之道。人之可以用第三義之道,代替第二義之道,是因為人本來是萬物之一,而居於萬物之中;人之所以知道有為萬物的本始或本母的道體,惟有依賴逆溯萬物的自我認知,並由這別異於萬物的自我認知的本始本母的道體的相狀,而默識這道體;人固然可以道相來相攝道體,進而以說明道相的言辭來指向「道」,從而意識到道相即是道體的意義;而觀見道相或依循道相來觀察世間,即是等同於觀察「道」了。《老子》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說「天下萬物生於有」,這個「有」應是指眼見之道,而這個「有」固然只是如上面所說的道、相、名,所以只是以道相的名字來說「道」。「有生於無」,所謂道之生物,是說相對於生物之前的無物,這即是道之動。道一方面是無物,另一方面是生物,所以「道」是同時兼備有相和無相;如此有生於無的「無」,即所以稱為眼見之道。然而,這裡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又生於無,但並不說「道」。這樣即是以道的「有相」與「無相」統攝道,也就是,我們可以用道相跟我們意識到的道作相同的理解。又二十五章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而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既然可以用道來作為名字,也就可以用大、逝、遠、反等不同的名字來稱謂它。這裡所說的大、逝、遠、反,都只是形容詞用來形容道所運行的相狀,也是用道相來指出眼見之道的道體,而我們意識到道的意義,它的力用的相狀也可用大、逝、遠、反來表示。除了上文的有、無等作為道相之外,如老子也說道是常、久,又說道生一,這裡「常」、「久」、「一」,也可了解為道相。而老子說知常即是知道,襲常即是襲道,抱一即是道,這樣則說明以道相來表顯「道」了。老子說道法自然,表示道是法爾如是。這裡所講「自然」亦只是道相,而並非實體。老子第一章說了道之有名、無名、常無、常有之後,又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即是說,玄和妙都兼備了有無二相的道相。 (4)同德之道 (5)修德或生活之道 (6)作為事物及人格心境狀態之道 《老子》十六章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這裡所說的「知常」「容」而「公」,可直接說為人能知「道」、行「道」,而有得於「道」的德性。然而,人既有這德性,其他人也看見了他有這德性,於是其他人即可以這德性來形容這個人。這即是說,前面第四義之道(同德之道)與這第六義之道,本來是可以相通的。但是,這中間還是有毫釐的分別,分別在於這人有德性,是這人作為主體而說這德性屬於他這個人自己的。這中間所重視的是人。至於以德性的相狀來形容這個人,只是由於這個人的德性合乎德性所應有的標準,然後才以德性來形容這個人。這裡所重視的是德性。以上二種意義,是不可以混淆的。所謂「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的意思是,這個有德之人,他能容納、能公正,他的心境和人格形態,即等同於王,同於天,而且同於道,也同於道的長久。這裡的同於道,即是有一合於道的心境和人格形態,而這道和道的長久,就可轉化為這個人的心境和人格形態的形容詞。這個道和道的長久,都是依人而說,因此,下文即說「沒身不殆」。意思是,没身是說我們這個生命,活到最後一口氣不來,死後骨頭化成灰塵,肉體沒有了,但精神卻永遠常存。殆,即盡的意思。肉身雖然有生老病死,但靈性永生不滅。人得了「道」,則身體雖然死了而道常存。 《老子》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這一章所講的保此道,如果直接指為形而上之道,那就很疏遠而不覺貼切。如果直接指為前文所說「靜之徐清,動之徐生」等,這裡所講的意義則較為貼切,而這道即是指修德積德的方法來說,是屬於上述的第五義之道。然而,如果通觀全章的內容,所謂保此道,亦可以是遍指「強為之容」以下所說的為善的人的心境和人格狀態,而這人確切的保存和任持這「道」。若是如此,這「道」的名稱,即是指人的心境和人格狀態是合於道的意義,而這「道」即是兼有人的心境和人格狀態的相狀的名稱。至於這一章所說「保此道者不欲盈」,則仍然可以說是「為無為,事無事」,所以,常常處於空虛的狀態而不會盈滿,這是以無功夫作為功夫,是修德積德的方法,用意是保存和任持這心境和人格狀態。然而這等功夫,亦只不過是微妙玄通的心境和人格狀態的自我保存和自我任持,除此之外,並沒有另外的功夫,或修德積德的方法。所以,這第六義之道即可以涵攝第五義之道。 這第六義之道以人的心境或人格狀態的名字作為「道」所表顯相狀的形容詞。這表顯相狀的形容詞,亦即是表狀這得道或有德性的心境和人格狀態所對外呈現的相狀。這對外所呈現的相狀,不管是對他人或對加以反省的心,可被稱為「人之道相」。這個得道的人內在具備德性,而且有他對外所呈現的道相,這好像形而上的道體所自具足的玄德,而呈現它的道相於人和物之前。這二個道相是可以相互相應的。因此,凡是依據上述第三義道相之道,把道等同於道相時,一切狀似這道和道相的表述,都可移用作為表述得道的人的心境和人格狀態,反過來說亦是一樣。《老子》十四章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這裡希、夷、微,都是用來形容形上道體的道相。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這裡的「玄」「妙」「微」,又可成為人的道相。這即是說,道體的道相和人的道相是可以相通的證明。只有形上道體的道相,猶如道體和它自身的玄德,自上而下的顯現而見;而得道的人的道相,是由人的積德修德工夫,及契合於道,由內而外所顯發。因此,這兩義的道相,仍然是不同的。老子所講得道者的心境和人格形態上所呈現的道相,除了上述第十六章外,二十章中大部分也說到這意義。以人的道相,依據於他所得於道的德性;這正好像形而上的道體的玄德,作為這道體的道相如玄、妙等所依持;所以老子之學的色彩,是更重視道體玄德的本身和人的內在德性的本身。 以老子和莊子來比較,老子思想中的形上道體,實有深隱而不可認識之處,而對於得道和有德性的人,他得道和所表顯的德性,亦有深隱而不可認識之處;至於莊子思想,他主張放任德性而行,充滿德性的內心完全表現出來,當中的深隱也全幅的呈現出來,由於德性充滿而形顯於外,他的精神就可以與萬物融為一體而游化其中。《莊子‧天下篇》論述老子說:「建之以常無有」「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澹然獨與神明居」。意思是說,老子之道還有內外本末之分,由於變化而回復到原本。至於對莊子的論述是說:「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歟生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其於本也,深閎而肆」「不敖倪於萬物」。意思是說,莊子之道是居無定所,而且無所不往,更加沒有本末內外常變的相對義,這樣的游心於萬化,就可以與天地精神相互往還了。這種境界固然有別於老子,而莊子思想的精義,亦可以不需要先建立一形而上的道體。莊子全書所講及的至人,天人,真人,都是就這個人的心境和人格狀態所具備的道相上面來說,同時就著這個人的道相的存在,而作為道體的存在。這正是以人的道相作為道的意義,當中特別重視人的道相來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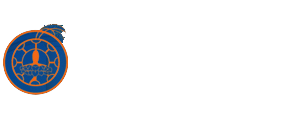 |
E-Learning Programs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