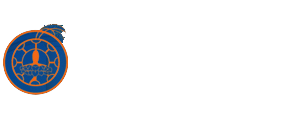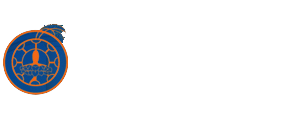法显大师译《大般泥洹经》的意义
法显大师回国以后所从事的译经活动及其所译的《大般泥洹经》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开创性影响。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法显大师从天竺、师子国带回建康的十一部经律,法显大师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一起合作译出六部,凡六十三卷。除二部律本之外,其余四部译经为:《大般泥洹经》六卷、《方等般泥洹经》二卷、《杂阿毗昙心》十三卷、《杂藏经》一卷。其中,《杂阿毗昙心》属于小乘毗昙学,《大般泥洹经》为大乘《涅槃经》的初译本,而《方等大般泥洹经》则是《长阿含经·游行经》的异译。从对佛教义学的影响而言,《杂阿毗昙心》的传译推动了佛教毗昙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大般泥洹经》的译出简直就像一声惊雷,在佛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更有道生法师以“涅槃圣”的雄姿出现,由此而使中国佛教发生了历史性转向。在此,谨将《大般泥洹经》产生的影响略作申论。
关于《大般泥洹经》翻译的经过,〈六卷泥洹经记〉这样说:”摩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如来平等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在座有二百五十人。“
此文虽未明言法显大师在翻译《大般泥洹经》之中的贡献,但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法显译经携回经律”项下注曰:“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沙门释法显“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而在同书同卷《般泥洹经》项下则署为“释法显出《大般泥洹经》六卷”。可见,此经的译出,法显的功劳非小,因此现今流传的版本均署名“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六卷《大般泥洹经》一经翻译完成,就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据叡法师说:“此《大般泥洹经》既出之后,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少惑。”更有彭城僧嵩“法师云:‘双林灭度,此为实说。常乐我净,乃为权说。故信《大品》而非《涅槃》。”据《高僧传》记载,僧嵩嵩“亦兼明数论。末年僻执,谓佛言佛不应常住,临终之日,舌本先烂焉。”而《出三藏记集》又说,僧嵩的弟子僧渊“诽谤《涅槃》,舌根销烂。”汤用彤先生怀疑“此事不见于《高僧传》,恐系僧嵩事误传。”而《高僧传》卷八《僧渊传》明言僧渊为僧嵩弟子,因而二僧师徒相承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以为不能轻易否定《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僧祐又说:“昔慧叡法师久叹愚迷,制此〈喻疑〉,防于今日,故存之录末。虽于录非类,显证同疑。”这段写于上引文末的话语,透露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尽管《涅槃经》已经流行已久,但时至僧祐编《出三藏记集》之时,仍然有人怀疑《涅槃经》的真实性。正是为了反击这种论调,僧祐才不惜破坏《出三藏记集》的体例而特意将《喻疑论》收入此书中。
显然,僧嵩、僧渊对于《大般泥洹经》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反击这种对《大般泥洹经》的非议,叡法师便专门撰写了《喻疑论》以正视听。
在《喻疑论》中,叡法师讲道:“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容书之家忽然起火。三十余家,一时荡然。写经人于火之中求铜铁器物,忽见所写经本在火不烧,及其所写一纸陌外亦烧,字亦无损。余诸纸巾,写经竹筒,皆为灰烬。”而同样的事情,《出三藏记集·法显传》则记载为:
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扬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
上述记载很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这一事件之所以流传甚广,从反面说明了当时争论的激烈。也就是说,《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使法显陷入了争论的旋涡无法自拔,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建康从事译经活动了。不过,法显大师的离去并未平息这场争论。因为此经的佛学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实在是太重大了。其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如来藏思想由此代替了大乘般若学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