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叫「玄學」?
「玄學」指《易經》、《老子》、《莊子》等三部經典,又稱「三玄」。玄學思想淵源(1)於「建安(2)文學」的主題發展而來,代表人物為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孔融、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㻛、阮瑀。建安風骨是指自由質樸、視野開闊、樂觀進取的面向封建秩序嚮往和激情。結合儒家的積極用世和道家的自由適性,學養、文學、藝術互攝融通,情深感性、思維精密、文采斐然、說理詳實,充分表現出一個時代的思潮,反映出該時代普遍流行的社會風氣──風流倜儻的高尚人格。
甚麼叫「名教」?
漢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漢儒注三經,注重章句訓詁,「以名為教」的經學研究是穩健而保守的。「名教」把宗法制度及與之相應的倫理道德觀念立名份、名目、名號、名節,一重名聲與教化,二重正名定分的禮教,「名教」即是維護宗法制度的道德禮教,確立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範疇。
漢末蔡邕:『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故尊卑永固,而不踰名教。』
玄學對名教的檢討?
東漢末,經歷五胡十六國後,魏曹丕稱帝(公元220),他至少有三次復興儒學之舉,但社會批判思潮的興起,玄學家注三經,由漢代重章句的繁瑣訓詁,轉為重於發揮義理。此時的玄學家,通過經義,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甚至可以借題發揮,打破學術風氣,啟發人們獨立思考。
嵇康:『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晉人袁宏:『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南朝鄭鮮先:『名教大極,忠孝而已。』
玄學對名教的發展?
「正始」是魏邵陵厲公的年號(公元240-248)。這時期的學風,上承漢末的淵源──儒家尚「名教」,下啟六朝的流變──道家尚「自然」,轉捩點是縱合後變成「玄學」,故名為「正始玄音」。魏晋玄學興盛40餘年,內容是承認「名教」,嚮往「自然」,重名教與自然之辨。不同流派對「名教」有不同的認識和主張,但思想原則是一致的,把獨論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合,通過道家的自然觀,淨化儒家的倫理綱常思想。以道融儒,提昇「外道內儒」的人文本質。此時的玄學風格明朗志遠、天真浪漫、豪情止禮、貴生適性地表現命運的悲壯與現實的苦難生活。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曾經指出當時的法家、名家、儒家、墨家、雜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高於各家,又不遺漏各家的長處。即玄學不只是儒道兩家思想發展的結合,而是哲學思想從兩漢獨儒後走到困境,再回歸到縱合百家思想的活潑跳脫,以道融儒,援儒入道的境況。
以玄學發展的三個階段來看…
何晏、王弼不特重「名教」,但也不主張廢棄「禮教」,強調「自然」與「名教」的聯繫。屬溫和派。
嵇康、阮籍初則徹底反對「名教」,沉淪於「自然」與「名教」的對立,終又認為只要順應人的無知、無欲、無情感、無好惡的潛意識或無意識去做,便能實現仁義道德。屬放任浪漫的激烈派。
向秀、郭象則強調了「自然」與「名教」的同一。認為「名教」內自有樂地,棄名教全任自然,是有體無用,不可棄「用」來談「體」,不可去「有」以存「無」,論證了任自然本性之所以能夠實現名教的根據。
玄學理論,原是上承魏初「名教」思想演變的。玄學家們就這樣在倡興老、莊之學的外象下,迂回曲折地,把儒學從漢代經學形式的衰竭中解救出來,實質上,是豐富和發展了儒學。
參考:
(1)佛教與中國文化第六講講義
(2)湯用彤《魏晉玄學•卷六》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註釋:
(1)余敦康(1930-2019),祖籍湖北。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史、哲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曾參與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秦漢卷和魏晉南北朝卷的寫作。著《何晏王弼玄學新探》、《易學今昔》、《內聖與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詮釋》、《中國哲學發展史》(合著)、《中國哲學論集》、主編《易學與管理》、《周易管理學》
(2)「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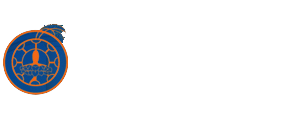
玄學對漢代名教的檢討與發展
名教的概念:“名教”一词,较早见于《管子·山至数》:“名教通于天下而夺其下。”这一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流行。关于名教的含义,本文认为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尤以君臣父子两伦及相应的忠孝为根基。郑鲜之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隋文帝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历俗敦风,宜见褒奖。唐太宗诏曰: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由此可见,名教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三纲五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名教即礼教。此外,名教的含义也近于“德教”、“王教”、 “风教”、 “儒教”。称为“礼教”,系侧重于礼仪有助教化;称“德教”是取其道德之义,称“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风教”是着眼于风俗与教化的联系,称“儒教”是因名教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所谓“以名为教”,即指依据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确定名分,名位,名节,名目,名号及善名,德名,荣名,令名,华名,以此来发挥劝善戒恶的道德感化功能。
玄学的概念:玄学,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名教与自然话题的由来,无疑是与东汉末叶以降儒家道德的危机息息相关。而这种道德危机的主要表现形态便是名实的脱节。
儒家本就是从春秋时为贵族相礼作乐的搢绅先生蜕变而来的,其与宗法社会的礼节风俗有着天然的联系。春秋末叶的孔子给原始的宗法性礼俗注入了较多道德意义,建构了一套伦理体系,从而亦创建了儒家学派。儒家伦理与礼俗的结合,既是它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废的一个秘密,又为其流于形式化、具文化和虚伪假冒造成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儒学与政治又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赏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伦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统治者又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感染教化的功能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运转。道德的标准遂成了政治上迁升贬黜的重要尺度。儒学与政治的联姻,既是儒学的幸运又是不幸,尽管汉武帝以来儒家便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跃居为强势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由于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必然造成儒学的蜕化与沉沦。
汉代儒生,在这种名利的引诱和权势的威逼下,大多失去了传统上“处士横议”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追求,一味循循娖娖,卑躬折节,奔竞于功名利禄之途。而名教虚伪化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的脱节。这种情况随着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政治危机而愈加恶化,终于演化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魏晋之际的司马氏集团,一方面闻名于“博学洽闻,伏膺名教”,“履义执忠”,“以至孝闻”,“孝弟忠信”,另一方面又自我放纵情欲,生活糜烂已极,如以孝显达的何曾日食万钱,其子日食二万,却仍言餐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名教无以维系人心,也无以维系社会,于是出现了任达不拘、矜高浮诞、肆意放荡、毁方败常的名士风潮。
儒“贵名”,法“崇实”,但二家都主张捏合名实;道家则夸大名实的离异而主张“无名”,甚或“忘象”,他们“尚虚”。就此而言,玄学名士沿袭了道家的思维路数。
玄学家们对语言的功用普遍具有怀疑态度。王弼说”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
何晏说“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
这是讲,名起于对事物有所肯定或否定,赞誉或贬损,其功用在于区别。而至美大爱无以名之,因为名称就是局限,有局限就非尽善尽美。所以,圣人应无名无誉。玄学家还认为,言辞概念不仅不能概括客观存在,也不能反映主观意念。关于后者,玄学家从言意之辨的角度加以论证。《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外物篇》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在玄学家们看来,由以名为教导致的矜名、尚名、显名这种道德语言的滥用,造成尚名好高,心迷神荡,丧情失真,欺世盗名,遂致是非混淆,天下多故。道德教化没有促成道德的普遍实现,而恰恰成了道德沦丧的祸源。正是出于这种洞识,他们蔑弃儒家标榜的道德名目、经典和圣人。
从上述所引玄学家的思想资料来看,“不言之教”包括如下内容:
一,否定仁、义、忠、孝等道德术语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说教的合理性;
二,否定儒家和统治者所定立与称颂的名位、德名的荣耀;
三,否定对尧、舜、周、孔等古圣人、贤人之名的称颂和追慕;
四,否定把六经等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字奉为神圣与顶礼膜拜。
玄学家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道德理念的最终实现。王弼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
“自然”概念有“无为”之义,如王弼解释《老子》“道常无为”句为:“顺自然也”。3而无为思想在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上,便表现为不言、无名。玄学家们主张用“不言之教”、“不言为化”来取代“以名为教”,认为如此才能保证道德的纯洁性,终而达于道德的普遍实现。应该说,这种思想源于道家,“不言之教”就是由老、庄首先提出来的,《老子》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同书四十三章曰:“是以知无为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庄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然,不同的是,老、庄虽然认为废弃外在的道德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
玄学的“自然”范畴,其含义之一指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然。他们认为,文教礼俗,礼乐教化是有害于自然圆满之人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内在的人类本性的关系。他们主张“越名任心”,“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说”人待教迹而后仁义者,非真性也。夫率真性而动,非假学也。故矫性伪情,舍己效物而行仁义者,是减削毁损于天性也。“嵇康更明言” 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任何一种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都或多或少是以牺牲个人的自我幸福来调整人们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玄学家把社会外在的名教与人性内在的自然对立起来,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感性因素理解为人性的基本因素,这似乎是感性的觉醒,理性的飞升。玄学家们蔑弃外在的礼仪教化,而提倡因任内在的道德情感。
这样,玄学家在人性方面,初而否定了桎梏自然人性的外在的仁义,终而又认定仁义是人的内在规定性。玄学家关于仁义是人之性情的说法似乎回到了儒家孟子,但又有所区别。孟子提出性善论是为了论证后天存养与教化的合理性,而玄学家的人性理论恰恰是为了否定它。
玄学名士们都把宇宙或宇宙的本源称之为“自然”,并把“自然”理解为宇宙或宇宙本源的属性。这种作为宇宙或宇宙本源之属性的自然,其内涵即是无为。当然,自然无为,不是讲绝对的无所施为,而是指无意识、无目的、无情感地循自然规律而为,一如四时代序,日夜更替,行云流水,花开花落那样自然而然。玄学家亦认为,人出之于天,故其与天有着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自然。天地是自然的,源之于大自然的人类也应合德天地,因任自然,复归自然。在玄学家那里,自然既是天的属性,又是人的属性,天与人统一于自然。自然沟通了人伦物理,天上人间。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两大主干的儒、道两家在思想的运演方法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上迥然有别。儒家的精髓是“中庸”,其对矛盾采取中庸调和的态度,因而他们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的礼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及其内在化的途径—教化,他们是宗法等级专制社会的“价值的立法者”,并因此被意识形态化。道家的核心是“无为”,其对矛盾采取回避和消解的方法,他们认定人为及其结果—文明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他们是否定式的哲学家,怀疑论者,似是现实社会的“价值的破坏者”。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他们秉承了老庄“无”的思维路数,而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又大体上肯认或口头上肯认儒家标榜的道德准则。他们从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不同层面,对名教与自然之辨做了由表层到深层,由微观到宏观的探讨。在反映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实与名、情与礼、古与今和天与人这四对矛盾中有着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玄学家对这四对矛盾采取了一种“还原法”,即在形式上肯定作为本源的前者而否定作为派生物的后者或其属性,通过取消矛盾双方的对立项来化解矛盾,这叫做“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玄学家的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用自然净化名教,否定以名为教的名教的教化形式而肯定仁、义、忠、孝等名教的本质内容。
参考:
1.《全晋文》卷四十七
2.《世说新语·德行》
3.阮籍,《咏怀诗》
4.《老子》三十七章及王弼注。
5.阮籍:《达庄论》
6.陈寅恪说:“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7.张海燕,《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http://lishisuo.cass.cn/zsyj/zsyj_sxsyjs/201210/t20121015_1794092.shtml
玄學對漢代名教的檢討與發展
名教的概念:“名教”一词,较早见于《管子·山至数》:“名教通于天下而夺其下。”这一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流行。关于名教的含义,本文认为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尤以君臣父子两伦及相应的忠孝为根基。郑鲜之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隋文帝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历俗敦风,宜见褒奖。唐太宗诏曰: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由此可见,名教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三纲五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名教即礼教。此外,名教的含义也近于“德教”、“王教”、 “风教”、 “儒教”。称为“礼教”,系侧重于礼仪有助教化;称“德教”是取其道德之义,称“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风教”是着眼于风俗与教化的联系,称“儒教”是因名教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所谓“以名为教”,即指依据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确定名分,名位,名节,名目,名号及善名,德名,荣名,令名,华名,以此来发挥劝善戒恶的道德感化功能。
玄学的概念:玄学,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名教与自然话题的由来,无疑是与东汉末叶以降儒家道德的危机息息相关。而这种道德危机的主要表现形态便是名实的脱节。
儒家本就是从春秋时为贵族相礼作乐的搢绅先生蜕变而来的,其与宗法社会的礼节风俗有着天然的联系。春秋末叶的孔子给原始的宗法性礼俗注入了较多道德意义,建构了一套伦理体系,从而亦创建了儒家学派。儒家伦理与礼俗的结合,既是它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废的一个秘密,又为其流于形式化、具文化和虚伪假冒造成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儒学与政治又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赏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伦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统治者又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感染教化的功能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运转。道德的标准遂成了政治上迁升贬黜的重要尺度。儒学与政治的联姻,既是儒学的幸运又是不幸,尽管汉武帝以来儒家便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跃居为强势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由于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必然造成儒学的蜕化与沉沦。
汉代儒生,在这种名利的引诱和权势的威逼下,大多失去了传统上“处士横议”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追求,一味循循娖娖,卑躬折节,奔竞于功名利禄之途。而名教虚伪化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的脱节。这种情况随着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政治危机而愈加恶化,终于演化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魏晋之际的司马氏集团,一方面闻名于“博学洽闻,伏膺名教”,“履义执忠”,“以至孝闻”,“孝弟忠信”,另一方面又自我放纵情欲,生活糜烂已极,如以孝显达的何曾日食万钱,其子日食二万,却仍言餐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名教无以维系人心,也无以维系社会,于是出现了任达不拘、矜高浮诞、肆意放荡、毁方败常的名士风潮。
儒“贵名”,法“崇实”,但二家都主张捏合名实;道家则夸大名实的离异而主张“无名”,甚或“忘象”,他们“尚虚”。就此而言,玄学名士沿袭了道家的思维路数。
玄学家们对语言的功用普遍具有怀疑态度。王弼说”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
何晏说“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
这是讲,名起于对事物有所肯定或否定,赞誉或贬损,其功用在于区别。而至美大爱无以名之,因为名称就是局限,有局限就非尽善尽美。所以,圣人应无名无誉。玄学家还认为,言辞概念不仅不能概括客观存在,也不能反映主观意念。关于后者,玄学家从言意之辨的角度加以论证。《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外物篇》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在玄学家们看来,由以名为教导致的矜名、尚名、显名这种道德语言的滥用,造成尚名好高,心迷神荡,丧情失真,欺世盗名,遂致是非混淆,天下多故。道德教化没有促成道德的普遍实现,而恰恰成了道德沦丧的祸源。正是出于这种洞识,他们蔑弃儒家标榜的道德名目、经典和圣人。
从上述所引玄学家的思想资料来看,“不言之教”包括如下内容:
一,否定仁、义、忠、孝等道德术语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说教的合理性;
二,否定儒家和统治者所定立与称颂的名位、德名的荣耀;
三,否定对尧、舜、周、孔等古圣人、贤人之名的称颂和追慕;
四,否定把六经等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字奉为神圣与顶礼膜拜。
玄学家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道德理念的最终实现。王弼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
“自然”概念有“无为”之义,如王弼解释《老子》“道常无为”句为:“顺自然也”。3而无为思想在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上,便表现为不言、无名。玄学家们主张用“不言之教”、“不言为化”来取代“以名为教”,认为如此才能保证道德的纯洁性,终而达于道德的普遍实现。应该说,这种思想源于道家,“不言之教”就是由老、庄首先提出来的,《老子》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同书四十三章曰:“是以知无为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庄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然,不同的是,老、庄虽然认为废弃外在的道德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
玄学的“自然”范畴,其含义之一指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然。他们认为,文教礼俗,礼乐教化是有害于自然圆满之人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内在的人类本性的关系。他们主张“越名任心”,“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说”人待教迹而后仁义者,非真性也。夫率真性而动,非假学也。故矫性伪情,舍己效物而行仁义者,是减削毁损于天性也。“嵇康更明言” 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任何一种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都或多或少是以牺牲个人的自我幸福来调整人们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玄学家把社会外在的名教与人性内在的自然对立起来,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感性因素理解为人性的基本因素,这似乎是感性的觉醒,理性的飞升。玄学家们蔑弃外在的礼仪教化,而提倡因任内在的道德情感。
这样,玄学家在人性方面,初而否定了桎梏自然人性的外在的仁义,终而又认定仁义是人的内在规定性。玄学家关于仁义是人之性情的说法似乎回到了儒家孟子,但又有所区别。孟子提出性善论是为了论证后天存养与教化的合理性,而玄学家的人性理论恰恰是为了否定它。
玄学名士们都把宇宙或宇宙的本源称之为“自然”,并把“自然”理解为宇宙或宇宙本源的属性。这种作为宇宙或宇宙本源之属性的自然,其内涵即是无为。当然,自然无为,不是讲绝对的无所施为,而是指无意识、无目的、无情感地循自然规律而为,一如四时代序,日夜更替,行云流水,花开花落那样自然而然。玄学家亦认为,人出之于天,故其与天有着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自然。天地是自然的,源之于大自然的人类也应合德天地,因任自然,复归自然。在玄学家那里,自然既是天的属性,又是人的属性,天与人统一于自然。自然沟通了人伦物理,天上人间。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两大主干的儒、道两家在思想的运演方法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上迥然有别。儒家的精髓是“中庸”,其对矛盾采取中庸调和的态度,因而他们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的礼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及其内在化的途径—教化,他们是宗法等级专制社会的“价值的立法者”,并因此被意识形态化。道家的核心是“无为”,其对矛盾采取回避和消解的方法,他们认定人为及其结果—文明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他们是否定式的哲学家,怀疑论者,似是现实社会的“价值的破坏者”。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他们秉承了老庄“无”的思维路数,而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又大体上肯认或口头上肯认儒家标榜的道德准则。他们从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不同层面,对名教与自然之辨做了由表层到深层,由微观到宏观的探讨。在反映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实与名、情与礼、古与今和天与人这四对矛盾中有着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玄学家对这四对矛盾采取了一种“还原法”,即在形式上肯定作为本源的前者而否定作为派生物的后者或其属性,通过取消矛盾双方的对立项来化解矛盾,这叫做“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玄学家的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用自然净化名教,否定以名为教的名教的教化形式而肯定仁、义、忠、孝等名教的本质内容。
参考:
1.《全晋文》卷四十七
2.《世说新语·德行》
3.阮籍,《咏怀诗》
4.《老子》三十七章及王弼注。
5.阮籍:《达庄论》
6.陈寅恪说:“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7.张海燕,《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http://lishisuo.cass.cn/zsyj/zsyj_sxsyjs/201210/t20121015_1794092.shtml
玄學對漢代名教的檢討與發展
名教的概念:“名教”一词,较早见于《管子·山至数》:“名教通于天下而夺其下。”这一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流行。关于名教的含义,本文认为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尤以君臣父子两伦及相应的忠孝为根基。郑鲜之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隋文帝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历俗敦风,宜见褒奖。唐太宗诏曰: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由此可见,名教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三纲五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名教即礼教。此外,名教的含义也近于“德教”、“王教”、 “风教”、 “儒教”。称为“礼教”,系侧重于礼仪有助教化;称“德教”是取其道德之义,称“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风教”是着眼于风俗与教化的联系,称“儒教”是因名教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所谓“以名为教”,即指依据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确定名分,名位,名节,名目,名号及善名,德名,荣名,令名,华名,以此来发挥劝善戒恶的道德感化功能。
玄学的概念:玄学,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名教与自然话题的由来,无疑是与东汉末叶以降儒家道德的危机息息相关。而这种道德危机的主要表现形态便是名实的脱节。
儒家本就是从春秋时为贵族相礼作乐的搢绅先生蜕变而来的,其与宗法社会的礼节风俗有着天然的联系。春秋末叶的孔子给原始的宗法性礼俗注入了较多道德意义,建构了一套伦理体系,从而亦创建了儒家学派。儒家伦理与礼俗的结合,既是它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废的一个秘密,又为其流于形式化、具文化和虚伪假冒造成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儒学与政治又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赏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伦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统治者又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感染教化的功能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运转。道德的标准遂成了政治上迁升贬黜的重要尺度。儒学与政治的联姻,既是儒学的幸运又是不幸,尽管汉武帝以来儒家便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跃居为强势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由于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必然造成儒学的蜕化与沉沦。
汉代儒生,在这种名利的引诱和权势的威逼下,大多失去了传统上“处士横议”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追求,一味循循娖娖,卑躬折节,奔竞于功名利禄之途。而名教虚伪化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的脱节。这种情况随着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政治危机而愈加恶化,终于演化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魏晋之际的司马氏集团,一方面闻名于“博学洽闻,伏膺名教”,“履义执忠”,“以至孝闻”,“孝弟忠信”,另一方面又自我放纵情欲,生活糜烂已极,如以孝显达的何曾日食万钱,其子日食二万,却仍言餐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名教无以维系人心,也无以维系社会,于是出现了任达不拘、矜高浮诞、肆意放荡、毁方败常的名士风潮。
儒“贵名”,法“崇实”,但二家都主张捏合名实;道家则夸大名实的离异而主张“无名”,甚或“忘象”,他们“尚虚”。就此而言,玄学名士沿袭了道家的思维路数。
玄学家们对语言的功用普遍具有怀疑态度。王弼说”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
何晏说“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
这是讲,名起于对事物有所肯定或否定,赞誉或贬损,其功用在于区别。而至美大爱无以名之,因为名称就是局限,有局限就非尽善尽美。所以,圣人应无名无誉。玄学家还认为,言辞概念不仅不能概括客观存在,也不能反映主观意念。关于后者,玄学家从言意之辨的角度加以论证。《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外物篇》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在玄学家们看来,由以名为教导致的矜名、尚名、显名这种道德语言的滥用,造成尚名好高,心迷神荡,丧情失真,欺世盗名,遂致是非混淆,天下多故。道德教化没有促成道德的普遍实现,而恰恰成了道德沦丧的祸源。正是出于这种洞识,他们蔑弃儒家标榜的道德名目、经典和圣人。
从上述所引玄学家的思想资料来看,“不言之教”包括如下内容:
一,否定仁、义、忠、孝等道德术语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说教的合理性;
二,否定儒家和统治者所定立与称颂的名位、德名的荣耀;
三,否定对尧、舜、周、孔等古圣人、贤人之名的称颂和追慕;
四,否定把六经等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字奉为神圣与顶礼膜拜。
玄学家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道德理念的最终实现。王弼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
“自然”概念有“无为”之义,如王弼解释《老子》“道常无为”句为:“顺自然也”。3而无为思想在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上,便表现为不言、无名。玄学家们主张用“不言之教”、“不言为化”来取代“以名为教”,认为如此才能保证道德的纯洁性,终而达于道德的普遍实现。应该说,这种思想源于道家,“不言之教”就是由老、庄首先提出来的,《老子》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同书四十三章曰:“是以知无为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庄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然,不同的是,老、庄虽然认为废弃外在的道德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
玄学的“自然”范畴,其含义之一指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然。他们认为,文教礼俗,礼乐教化是有害于自然圆满之人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内在的人类本性的关系。他们主张“越名任心”,“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说”人待教迹而后仁义者,非真性也。夫率真性而动,非假学也。故矫性伪情,舍己效物而行仁义者,是减削毁损于天性也。“嵇康更明言” 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任何一种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都或多或少是以牺牲个人的自我幸福来调整人们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玄学家把社会外在的名教与人性内在的自然对立起来,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感性因素理解为人性的基本因素,这似乎是感性的觉醒,理性的飞升。玄学家们蔑弃外在的礼仪教化,而提倡因任内在的道德情感。
这样,玄学家在人性方面,初而否定了桎梏自然人性的外在的仁义,终而又认定仁义是人的内在规定性。玄学家关于仁义是人之性情的说法似乎回到了儒家孟子,但又有所区别。孟子提出性善论是为了论证后天存养与教化的合理性,而玄学家的人性理论恰恰是为了否定它。
玄学名士们都把宇宙或宇宙的本源称之为“自然”,并把“自然”理解为宇宙或宇宙本源的属性。这种作为宇宙或宇宙本源之属性的自然,其内涵即是无为。当然,自然无为,不是讲绝对的无所施为,而是指无意识、无目的、无情感地循自然规律而为,一如四时代序,日夜更替,行云流水,花开花落那样自然而然。玄学家亦认为,人出之于天,故其与天有着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自然。天地是自然的,源之于大自然的人类也应合德天地,因任自然,复归自然。在玄学家那里,自然既是天的属性,又是人的属性,天与人统一于自然。自然沟通了人伦物理,天上人间。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两大主干的儒、道两家在思想的运演方法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上迥然有别。儒家的精髓是“中庸”,其对矛盾采取中庸调和的态度,因而他们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的礼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及其内在化的途径—教化,他们是宗法等级专制社会的“价值的立法者”,并因此被意识形态化。道家的核心是“无为”,其对矛盾采取回避和消解的方法,他们认定人为及其结果—文明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他们是否定式的哲学家,怀疑论者,似是现实社会的“价值的破坏者”。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他们秉承了老庄“无”的思维路数,而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又大体上肯认或口头上肯认儒家标榜的道德准则。他们从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不同层面,对名教与自然之辨做了由表层到深层,由微观到宏观的探讨。在反映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实与名、情与礼、古与今和天与人这四对矛盾中有着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玄学家对这四对矛盾采取了一种“还原法”,即在形式上肯定作为本源的前者而否定作为派生物的后者或其属性,通过取消矛盾双方的对立项来化解矛盾,这叫做“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玄学家的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用自然净化名教,否定以名为教的名教的教化形式而肯定仁、义、忠、孝等名教的本质内容。
参考:
1.《全晋文》卷四十七
2.《世说新语·德行》
3.阮籍,《咏怀诗》
4.《老子》三十七章及王弼注。
5.阮籍:《达庄论》
6.陈寅恪说:“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7.张海燕,《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http://lishisuo.cass.cn/zsyj/zsyj_sxsyjs/201210/t20121015_1794092.shtml